人工智能船舶引領國際海事規則體系變革
發布時間:2019-10-11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使得船舶具有擬人智化特性,深深影響了以船長及船員為規制對象建立的國際海事公約體系。智能化是船舶駕駛技術發展的趨勢,國際海事公約以納入和轉化的方式融入我國國內法規則體系,二者在規則設計上具有相洽性。在法律層面因應船舶智能化發展方向,不僅需要關注相關國際規則變革,也需要考慮智能船舶領域的法律需求,從立法機制層面適應船舶智能化的新業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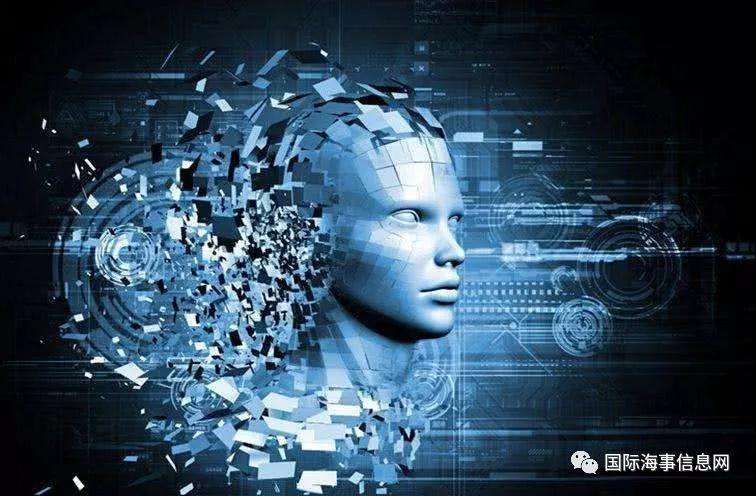
智能化引領國際航行船舶未來發展方向
人工智能船舶是人工智能技術在海事領域的重要應用成果,發展智能船舶已經成為國際航運界的共識。2017年12月,全球第一艘萬噸級智能船舶通過倫敦船級社認證,正式交付使用。同年,挪威、日本等國宣布在2019年推出用于國際航行的無人駕駛船舶。美國等國家已聯合向國際海事組織(以下簡稱IMO)提交人工智能船舶立法范圍的方案,國際海事委員會也已設立國際公約與人工智能船舶國際工作組,起草相關行為準則。我國商船船隊規模排名世界第三,人工智能船舶研發已經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中國船級社發布全球首部《智能船舶規范》,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目標。2018年12月工信部等部門聯合發布《智能船舶發展行動計劃(2019~2021年)》,對我國智能船舶發展頂層規劃提出具體方案。可見,全球范圍內人工智能船舶時代已經到來。
船舶智能化是航運技術與外部智能技術的融合。智能船舶的發展經歷了從局部到整體的漸進式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綜合船橋系統應用于船舶自動化駕駛至今,遠程測控技術、互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等科技成果不斷融入船舶駕駛技術,不同組織或團隊相繼公布了各自的智能船舶研發路線。英國勞氏船級社著重分析人與船舶的關系,側重于網絡支持方案。挪威船級社關注機載智能設備操作可用性,關注智能系統帶來的潛在風險。韓國現代重工推出綜合智能船舶解決方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和大數據提高船舶運營智能化水平。國際海事組織側重智能船舶技術路線圖,關注智能系統在不同階段的實現形式。殊途同歸,上述船舶智能技術的發展都是在不斷利用新技術改進船舶自主控制功能,在兼顧航行安全及運營效率優化前提下,通過不斷的技術融合提升船舶數字化水平。
國際海事公約因應船舶智能化趨勢的改革路徑
國際海事公約為海上航行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具有普遍適用性。截至2019年7月,IMO已經通過50余部有關船舶航行的國際公約或協定。這些公約或協定重點規制船舶裝置安全性能和駕駛人員安全駕駛技能,公約中的最低安全配員、適航性以及碰撞規則中的“良好的航海技能”等規則體系,在規制人工智能船舶時,均存在失靈的風險。由于商船航行活動具有跨國特征,對人工智能船舶的規制也需要在國際法層面達成共識。由于國際海事公約是以人工駕駛船的概念為基礎起草的,人工智能船舶的出現既沖擊了國際公約構建的海上航行規則,也為完善公約的既定原則和概念提供了“跳板”。
第一,以船長和船員為規制對象的規則體系面臨重構。人工智能船舶不僅是具有智慧性質的工具,也是可做出獨立意思表示的特殊主體,其獨立自主做出意思表示的能力一經實現,即表明智能船舶享有一定的法律人格。然而,它又不同于自然人或現有的擬制法人,人工智能船舶承擔行為后果的能力是有限的。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船舶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很難繼續將其歸為供人類驅使的被動工具。以人為“核心”的公約規則體系,對適航義務認定、救助義務履行等方面的規定,已經與智能船舶的發展不相適應。
第二,船舶控制權主體法律地位及其法律責任發生變化。人工智能船舶控制權主體包括船上控制者和岸基遠程控制者,雖然以上兩類主體的身份特征近似于船長及船員,但是智能船舶海上航行經由人工智能系統和控制人員實現交流。控制權主體的法律責任與人工智能系統的自主性程度相稱,即智能系統自主性程度越強,其他主體的控制責任就越弱,國際海事公約在“故意”與“過失”基礎上構建的法律責任體系不能完全適用于以上兩類主體。對于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船舶可以考慮賦予其有限的“人格”,同時基于船舶自身的財產屬性,將其從船舶所有人財產權中部分或全部剝離,作為智能船舶承擔法律責任的財產基礎。
第三,調整海上航行風險治理模式及國際合作路徑。當前人工智能技術遠未完美,基于對目前科技水平的審慎態度,國際海事組織正制定相關指南,在人工智能船舶海上航行風險治理中,推廣技術控制與法律控制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機制,采取預防性行為和因應性制度,對于人工智能引發的負面影響制定風險防治措施。國際合作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國際法也為各類國際合作建構可持續的法律框架。國際海事公約鼓勵各國利用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圍繞智能技術研發、航行規則修訂、技術標準制定、航行安全保障等方面開展交流與合作,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智能船舶發展國際合作機制與平臺,在全球層面推動法律標準與產業政策相協調的國際框架,不僅符合智能船舶的未來發展方向,也符合各國航運產業利益。
因應國際海事公約發展趨勢完善我國人工智能船舶立法
船舶立法在我國屬于海事立法范疇。國內海事立法對國際海事公約相關內容作了納入或轉化,形成了國內立法與國際公約相接洽的立法模式。因應船舶智能化時代變革,國內海事立法應立足于人工智能船舶發展新業態,參照相關國際公約發展趨勢,在為主管機關執行監管提供切實可行的法律依據的同時,逐步將人工智能船舶規制納入法治軌道。
一是明確人工智能船舶的屬性。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使得船舶具有擬人化特性,突破了船長及船員對船舶航行的絕對控制。如何認定人工智能船舶的法律屬性,關乎相應海上航行規則的適用及法律責任的認定。對此,國內法需要明確人工智能船舶屬于“船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船舶本質上依然是用于海上航行的可移動設備,服務于載人、載貨或其他交通運輸目的。人工智能船舶是否享有獨立法律人格,不僅在于其人智化的社會屬性,更需要考慮人格擬制與法律責任之間的彌合度。具備獨立財產是法律擬制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前提,從法益平衡出發,賦予人工智能船舶有限的法律人格,必然需要發揮財產制度的基礎性作用,否則就不可能模仿法人制度,對智能船舶設定獨立的責任。
二是采取技術控制與法律控制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機制。技術控制以風險預防為基本理念,設定從技術研發到應用過程的責任制度,法律控制應側重于對人工智能船舶的研發、使用和管理建立限制機制、禁止機制以及懲戒機制。技術規則法律化,是海事立法的特色及慣用方式,我國《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海事立法中的適航義務、避碰規則、停靠規則等規定,無一不是發端于技術規則,最后被立法吸納,演變成法律規則。國內立法在規范智能船舶時,尤其應當適時吸收中、外船級社制定的智能船舶技術標準,將比較成熟的技術標準轉化為法律規則。
三是將岸基遠程控制者納入法律責任體系。在船上配置船長、船員,不是智能船舶營運的必要條件,智能船舶的出現將挑戰現有法律中有關適航義務的規定。人工智能船舶進入海上運營已成定局,但短期內并不會取代傳統船舶。智能船舶出現后,船長履行的適航保證義務,將由岸上控制人員代為履行。岸基遠程控制者不等同于船長、船員,但基于其控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需要將其納入規制人工智能船舶海上航行法律責任體系,承擔相應的替代或補充責任。
四是對智能船舶海難救助義務作出減免性規定。《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5章第33條、《海洋法公約》第98條及我國《海上交通安全法》均規定,船長及船員應當履行救助的義務,盡力救助遇險的人員,不得擅自離開事故現場或者逃逸。部分人工智能船舶由于其自身結構特點,或者因船舶屬性及救生設備的配備狀況,決定智能船舶本身不具備良好的救援條件。海難救助義務的本質是互助義務,無人駕駛船舶因為不存在船上控制人員而降低了自身救助需求,從法益衡量出發,立法應減輕或免除岸基遠程控制者的救助義務,或者制定替代性解決方案,規定岸基遠程控制者應當履行通知義務,將海上人員遇險的信息轉移至其他具備救助能力的船舶或救助中心。藉此,對智能船舶控制者的海難救助法律義務做出相應減免。





 18678907213
18678907213 